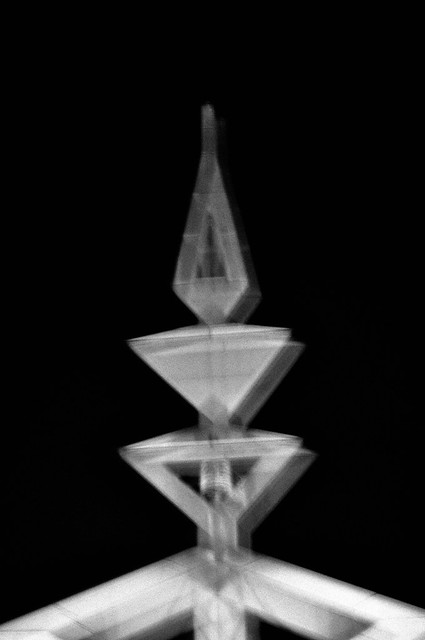靳菱菱的《認同的路徑:撒奇萊雅族與太魯閣族的比較研究》一書,旨在對族群認同議題進行探討,而這樣問題意識的背後,有作者出於公私兩方面的關切。在個人的層面,如作者於本書〈自序〉中所描述的,生在父親為外省人,母親為本省人的跨族群家庭,在生活的各個面向裡,總會不時面對認同的刻板印象,以及隨之而來的排擠和錯亂。在公眾層次上,族群認同一直是困擾著臺灣的難題,歷史發展的曲折糾葛,結合了政治立場的不同選擇,族群問題或顯或暗,一直都是這塊土地難以癒合傷。要直接回答如此龐大而深刻的問題,作者選擇了原住民作為研究對象,除了避開直接的政治紛擾,原住民雖僅佔臺灣2%人口,族群內部的構成卻十分複雜,本書的焦點置於撒奇萊雅族與太魯閣族兩者之間的比較,更是具有深意的選擇,兩者都在各自的正名運動中獨立,前者脫離阿美族,後者脫離太魯閣族,然而結果卻大不相同,撒奇萊雅族獨立過程平和,和阿美族未表示反對,然而雖然推動了許多文化復振運動,始終未建立起強烈的自我認同,族人仍遊走在撒奇萊雅族和阿美族之間;太魯閣族在脫離的過程中便受到賽德克族人的反對,並透過的教會和地方行政的協助下,開啟了完整的族群認同。同樣的起點,南轅北轍的結局,正突顯族群認同的複雜特質,提供了最佳的觀察點。
全書含緒論、結論共八章。諸論指出過去政治學領域對原住民研究的關注度有限,2000年原住民正名運動,新興族群形成程中建構論和原生論的討論,呼應了政治學的重要討論;並概述了撒奇萊雅族和太魯閣族的正名經過,以及研究方法與限制。第二章則對「認同」一詞進行了理論的回顧,除對原生論(primordialism,即認為人們會依語言、血緣、土地等先天要素,自動歸屬於固定的族類)和建構論(constructivism,強調族群是隨脈絡變化的後天聚合),並提供了認知心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待臺灣的族群認同。第三章則討論基督教和原住民族群認同的關係,基督教教義雖對原住民部落原有的信仰和文化帶來巨大的變化,長期下來亦覓得了共處的平衡點,反而讓原住民傳統得到保存,並成為原住民正名和族群運動重要支持力量。第四章則簡述了臺灣原住民正名運動的緣由和發展,指出正名運動主要運用「重新建構族群分類系統」、「尋找歷史」、「凝聚草根力量」、群眾動員等策略。在作者看來正名運動最主要的動機是為了公開宣示自己更明確的身份,區別和他者的差異。第五章和第六章則運用大量口述,分別概述了太魯閣族和撒奇萊雅族各自族群建構歷程,前者堅實的族群邊界,有其客觀條件的優勢,使得它能和他者進行明確區隔;後者則試著和學界、官方合作,重新「發明」傳統,結果族群的認同依舊游移。作者最後對兩者進行了比較,指出在策略上,都試圖找尋歷史的截斷點、發明與再現傳統、界定我屬群族範圍等手段,然而知識菁英和族人對正名目的的不同認知,結果造成了違背族人日常生活的習俗和記憶,「為強調區別而創造」,形成未與族人生命歷程結合的空中樓閣,「終究會淪為少數人自我安慰式的想像」。
我們或可將作者的說法,歸結為一種以原生論為基礎的建構論,或言指出認同建構的極限。是否能成立,則賴未來學界的檢視。無論如何,該書勾勒出了族群認同這個議題的複雜,它絕非一條有著明確指示的筆直道路,而是彎曲環繞、甚至滿是泥濘未有任何依憑的荒地,任何簡單的概括,或想當然的推測,都只會帶來更大的錯誤與災難。認識問題的難解,繼續努力地抽絲剝繭,或許比一刀兩斷地強作解人,更為重要,至少對族群認同問題應如此看待,或許是本書所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吧。